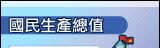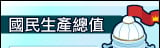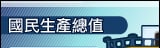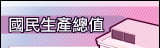本帖最後由 csy_ma 於 12-12-17 02:12 編輯
Ben2004 發表於 12-12-16 14:53 
在書中, 可看到這位培英家長為何決定放棄培英, 讓女兒在家上課homeschool. 書中提及作著對培英的校風和邱校長的觀感, 值得一看...
謝謝介紹,很有興趣知道,會找來看看的
只看過陳曉蕾對張惠侶的介紹:http://leilafeature.mysinablog.com/index.php?op=ViewArticle&articleId=3833149
升學不重要
張惠侶和香港一般家長很不一樣,她不介意兩個女兒文思文莉是否能升讀大學:「香港大中小學的校長,都是以進大學為目標,好扭曲。我當年是媽媽說不唸大學找不到工作,可是現在年代不同了,讀大學也未必找到工作、有錢、或者做到自己開心的事。」
這不是隨口批評,她加入過女兒學校的家教會,當過家教會主席、家長校董,上過中大教育學院的校董培訓班,並且因為工作不斷訪問香港的學校。
她認真思考教育目的:除了知識增長、判別是非,可以助解決生活中的各種挑戰,而不是像香港學校把學科成績和成長、未來成就掛釣。對兩個女兒,期望是愉快學習、愉快成長,成為對社會有貢獻,有責任感的人。「有了這素質,自然會做應做的事,比學科成績重要太多。」她說。
環遊世界五年
張惠侶的女兒很早便沒有去學校:一家四口坐帆船環遊世界了接近五年,在船上,爸爸退休水警警官Arni Highfield是負責訓話的校長,媽媽是執行的班主任,曾經監製港台節目《頭條新聞》的姨媽張惠儀,也上船一年當助教。
2005年初旅程開始時文莉六歲、文思四歲,爸爸查到帆遊的家庭多選用美國Calvert School的家教教材,上網訂購一年級和幼稚園的兩材教材,不但有英、數、科學等課本習作,還有美術用品和文具。「教師手冊好厚一本,只要你識字,跟著做就行。」張惠侶說得很輕鬆,夫婦都深信開眼界比待在課室重要,並不擔心日後上學有銜接問題。
 (在赤道學Equator) (在赤道學Equator)
每一天,都是「上課」:地理科、生物科、歷史科……兩個小女孩用電腦資料做報告,閱讀大量課外書,又跟著媽媽設計的工作紙學中文。偶然上岸,兩個女兒便會在當地學校上課,包括南太平洋偏遠小島的村校三天、紐西蘭北島的鄉村學校兩個月,澳州昆士蘭的中央小學兩星期等。
2009年底回到香港,一家四口去了六間小學面試,最後選擇了一間小型的屋邨津校,因為校長老師都很有心,學校推行融合教育,學生包括過度活躍症、聽障等。張惠侶還加入家教會,一年後當上家教會主席,成為家長校董。
扭曲的教育
「同學們,吃什麼肉?」英文老師兼班主任問。
「烏龜!」剛上學的文思興高采烈地說。
老師的反應是:別傻了,然後繼續問其他同學,文思那天好失落地回到家裡。如果當時老師追問一句:你有吃過嗎?其他同學也許有機會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會吃烏龜肉,也許也不會開始取笑文思的中文:「你咁無用!」
文莉比妹妹適應學校,可是升上中學後,每天回家都累得不說話,她寧願早點睡覺,天天清晨五點主動起來做功課。開學一個月,班主任在家長會說:「現在開課的蜜月期過了,學生要開始讀書啦。」張惠侶馬上舉手:「蜜月期?那怎樣才叫多功課?」其他家長也陸續發問,有個還哭了:「我晚晚都和孩子做功課到半夜!」
「香港上學就是這樣的了。」、「人人都這樣,難道你不做?」、「成績不好怎入大學?」這是一般香港家長的回應,但張惠侶想的是:「值不值得?」
學校不是社會
海上生活五年,連本地生活也得適應吧,離開學校,會否影響社交能力?
「可是學校根本不是自然的環境,上班會規定午餐也不能說話?上司會這樣高高在?香港學校裡的人際闗係,不是必然的。」張惠侶看到的,是兩年來,兩個女兒漸漸由充滿自信,滿腦子意見,變成對事物沒看法,問任何問題,多數回一個「聳聳肩」一臉沒所謂,每天都累得沒精打彩。
最初她還努力積極,請女兒留意學校裡有趣的事,放學後說三件,一連問了個多星期,三件趣事都是午餐吃了什麼,後來換了飯商,連吃飯也沒什麼好談了。「如果再待在香港的學校,女兒的健康和心智都有影響。」張惠侶認真地說。
可是這些不都是磨練?
「磨練可以有其他機會。」她回答得更快。兩個女兒都接受小風帆訓練,並且代表香港出賽,那是非常嚴格的訓練,然而對於學校都不看重。中學老師知道文莉將來有志代表香港出賽, 卻直接說:「讀書更要緊。」文思連報讀體藝中學,連面試機會也沒有。
張惠侶說之前和體藝中學的校長通了十次電郵,最後一封她寫道:「我以為文思起碼會有機會面試,你的決定,讓我們決心在家上課。」
感覺如下:
她兩個女兒自小沒有受過正規教育,較國際學校學生更難適應香港傳統學校的生活,張惠侶能選擇沙培,足證她認為沙培跟傳統的津中有很大分別。
不過,我挺懷疑她所說,會有學校規定午餐不能說話嗎?(肯定不是中一已放學生上街吃飯的沙培,要不然,不會有中一生樂於享受可買飯回課室吃的"特權")定這規矩,不是擺個無無聊聊的艱鉅任務給老師嗎?我不是說,張有可能說謊,但每個人都有其盲點,當她和她的女兒在跟整個社會主流價值對抗時,有些事就很難拉遠和寬容去看。
她可能離港太久吧?想不起整個香港社會對分數勢利的頑固程度有多大。說實話,假如沙培的老師對文莉說,儘管去練習參賽吧,學業就暫不用管了,那其他知悉事件的同學,會有什麼反應?她細女亦同為香港代表,但體藝就是不肯收她,為什麼?她也未免太高估一所傳統津中對抗主體價值的能力?
|  我的8歲女升小時已離棄一切有關公主的事物了......老人精.
我的8歲女升小時已離棄一切有關公主的事物了......老人精.

 沒獲獎的…那就要看您囝囝獲獎項目多不多?太多的,就要精,如沒體能的課外活動,填也不壞,有參賽證書嗎?
沒獲獎的…那就要看您囝囝獲獎項目多不多?太多的,就要精,如沒體能的課外活動,填也不壞,有參賽證書嗎?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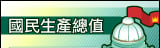



 發表於 12-12-17 02:11
發表於 12-12-17 02:11


 (在赤道學Equator)
(在赤道學Equator) ……
…… 但是,簡樸的生活,不見得對成長期的孩子全無好處?
但是,簡樸的生活,不見得對成長期的孩子全無好處? )
)